文/蔡亞庭(台灣障礙女性平權連線 前秘書長)
在Covid-19與障礙研究裡,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:
一、我如何透過我的障礙和性別經驗,成為「家裡的陳時中」
二、在2020年這場世界級防疫大作戰中,我的生活並沒有受到太多防疫措施的影響,其背後所透露出的照顧資源不足與「情感稅」
三、一個障礙者的經驗可以提供社會大眾提高疫情警覺性之處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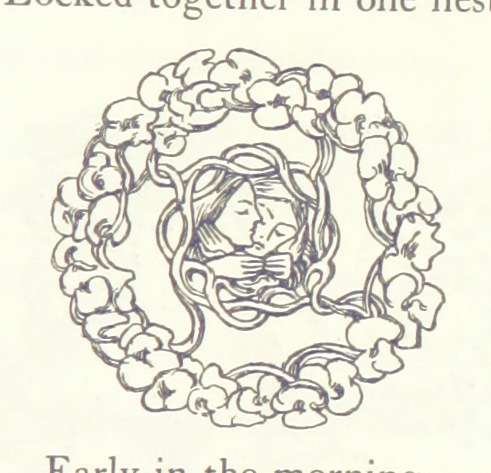
Rossetti, Christina Georgina. (1893) “Goblin Market … Illustrated by L. Housman. L.P”
∕收藏者:大英圖書館。無已知版權限制。
圖說:緊密和諧的照護關係,是由障礙者與提供照護者彼此關照的結果。 圖片來源:flickr
一、障礙身體及經驗累積而成的防疫知識庫
我在去年12月看到越來越多報導在講關於武漢肺炎的消息後,便注意到中國過年期間的境內移動,和世界各地的海外移動交互影響,以致年節期間的旅遊潮可能讓人們把病毒帶回台灣。
因此,我很早開始擔心並請家人先去買了三盒口罩,同時也跟家人一起在家中啟動防疫措施,包含回家的時候要先洗手、換衣服,然後出門要戴口罩,並且在過年返家的路途中,盡量不在休息站下車。
我比起陳時中還要超前部署。
能夠有這麼高的警覺性,是因為我有一個很容易受感染的身體。我從小到大的經驗是,人家在端午節、中秋節、寒暑假都是開心放假出門玩,我卻常因為感冒在住院。也曾經在SARS期間疑似黴漿菌感染,住進加護病房一個月,插了三次管,差點無法脫離呼吸器。
這樣頻繁因為小感冒而有生命危險的障礙經驗,讓我對於流行性疾病的傳染非常警覺,甚至警覺到只要身邊有人咳嗽打噴嚏,我都會感覺自己被傳染了、喉嚨開始痛了,像極了慮病症。對於疾病傳染的警覺心,以及比別人多次的治療經驗,讓我累積了一定的醫療知識和防疫技能,包含細菌與病毒的感染機制、人體的免疫機制、營養素的作用與特性、藥物的作用等等。
二、障礙、性別、生存需求與防疫
積極的防疫對我來說不只是照顧自己的健康,也是照顧家人的健康。身為需要密集支持的障礙者,我要活著就必須要獲得照顧支持。
因此,我對於家人,尤其是一直以來的主要照顧者的健康特別關注。除了充滿對家人的關心與愛,還存在著極度擔心因為照顧者失去健康而無法提供我協助,那時我就只能被迫失去妥善的照顧支持以及做人的尊嚴與自由。
此外,身為女性,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接收到、學習到、也被鼓勵地將照顧工作劃為自我成就感的來源之一,也被鼓勵提出情感性的關懷、細緻的觀察及同理。在照顧他人的實作中,障礙身體使我無法運用現今普遍的照顧提供方式 – 以身體勞動來提供照顧。但障礙經驗訓練我警覺環境中的感染風險、學習預防保健醫療知識、感知自身身體狀況的能力,促成我發展不同的照顧提供方式。女性經驗中被鼓勵感同身受、表達情感,每月感受賀爾蒙對身體劇烈影響的變化,也更加強我對自身狀況的感受性和觀察力。
值得一提的是,在SARS期間的住院經驗,我看到了醫護人員協助的質與量不足。我的主要照顧者為了讓我有更舒適的協助,進到沒有陪病設計的物理環境,只能坐著板凳、趴在床上睡了一個月,導致出院後許久,主要照顧者的身體一直很不好。
這也讓我發覺,照顧自己的身體健康,同時也是在照顧家人的健康。因此,一個支持需求密集的障礙女性之照顧工作的實作,便是無時無刻地照顧自己的健康,以及注意到環境中對健康的危險資訊和因應方法,並把它們提供給家人;照顧家人也成為我維持生存安全,以及對自我價值的認同方式。
三、未受疫情影響的生活 – 背後所透露的照顧資源不足與「情感稅」
對我來說,防疫後的生活和防疫前沒什麼不一樣。這個現象除了源於我的身體平時便處於防疫情境,還因為我有緊密的家庭支持及照顧。
我的主要照顧者一直都是我媽媽,從我出生到現在24小時全年無休,所以她非常熟悉我什麼時候需要協助、協助什麼、語言意思、協助技巧等等;我也了解她在協助的時候,習慣使用的力量大小、角度、節奏,以及能力等等。在疫情期間,因為對彼此狀態的掌握度、熟悉度與穩定度,讓我不用擔心使用我已經很少的體力,去不斷地教導其他不熟的協助人員(像是居服、個助、外籍看護)。
這樣的教導很耗力,也導致我的抵抗力更弱、更害怕疫情感染;擔心原本的照顧人員不能來了怎麼辦、一堆照顧者來來去去帶來病菌怎麼辦。
雖然緊密的家庭照顧關係可以提供密集的支持,但我平常也付出很多「情感稅」。高度的支持需求讓我需要做許多的「腦內工作」來維持任何的照顧關係,像是下意識地隨時觀察和掌握照顧者的動向,以利於揣測、推論照顧者的行動,並且自己在腦中先行安排協助行動的規劃。
又或者是在提出協助需求之前,判斷自己是否要求協助的頻率太高、是否能忍住且不提出需求,只有當需求能通過自己層層的把關與合理化的時候,才會提出來。在面對家庭照顧者時,我更需要堅守這些程序,來彌補我對家人的愧疚。
即便我基於人權與性別意識的反思,不想成為剝削和壓榨母親角色的共犯,但因為照顧支持資源量的不足,讓過往身體資源還夠的我,失去了進入其他協助關係,以及學習適應和教導其他協助者能力的機會。而照顧支持資源質的不足,則讓我進入家庭照顧以外的關係時有巨大的門檻,擺在眼前的不僅是金錢的支出,還有龐大的體力、管理、人際、情緒控管的消耗與能力要求。隨著我的身體障礙加重,我漸漸無法使用如速食般,一來就要進入完整的協助工作的照顧支持服務,而更加依賴媽媽的照顧。
四、疫情下,政府可以由障礙者的經驗學到什麼?
災害的防治、預測,需要高度的警覺性和敏感度。易受感染的障礙女性經驗,可以提供家人及政府對疫情的高度警覺性,以及關注疫情發生及擴散的可能性,進而更超前地部署、謹慎地行動,讓防疫不會因為一時的疏忽產生破口。另外,細緻的防疫政策也能讓防疫資源和措施,盡可能地回應多元需求的人們。
而沒有受到影響的防疫生活經驗,反映出政府照顧資源的量及質的不足,導致照顧工作落在家人(尤其是女性)的身上,形成彼此的負擔、牽絆。政府應該要正視障礙者與家庭照顧者在照顧關係中,產生大量的情緒協商或工作,以及自我究責、自我懷疑的情感稅,進而透過正式支持服務的提供,減少類似情境的出現。
本文原載於「障礙研究五四三」網站,為2020年臺灣障礙研究學會論壇蔡亞庭發言整理而成,獲得「台北大學社科院高教深耕計畫」贊助,並經過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兼系主任林昭吟修潤。論壇海報,請見全文最後圖片。

Tags: D249期電子報
